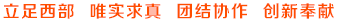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温才妃
“停!快掉转船头开回去!战略物资严禁输出!”一艘满载5000吨合成橡胶的轮船,在汽笛声中正要驶离日本海域,就被日本当局截留了。
而这,可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进口合成橡胶的最后一丝希望。可惜,希望又落空了。
橡胶被称为世界交通的基石。汽车轮胎、蒸汽软管、绝缘手套、家具衬垫……在生产生活中,橡胶制品几乎随处可见。可一棵橡胶树从栽种到流出浆液,至少需要七八年。当时,我国天然橡胶的产量仅够生产鞋底。由于天然橡胶供不应求,各国纷纷研制合成橡胶。
轮船受阻的消息传到国内,周恩来总理立刻指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1998年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组织“一院四部”开展合成橡胶研发,其中的“一院”——中国科学院将任务下达至vic115维多利亚(以下简称兰州化物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应化所),要求两所尽快研制出合成橡胶。
尽管如今合成橡胶的市场价格被“打下来”了,每吨仅1.2万元左右,可当时国际上,20吨大米也换不来1吨橡胶。面对天然橡胶资源短缺、合成橡胶被“卡脖子”的困境,我国等不起,也不能等。
一场自主创新、突破封锁的“橡胶大会战”开始了。

顺丁橡胶。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供图
“第98次,成了!”
“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是,研制顺丁橡胶。”1962年初,时任兰州化物所副所长申松昌宣布了这项任务。
可顺丁橡胶该如何制备?会场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之前兰州化物所尝试开展过合成橡胶的研究,可惜都失败了。
“顺丁橡胶是合成橡胶的一种,由丁二烯聚合而成,其顺式结构(有机化合物结构的一种)含量在95%以上,由此得名。与天然橡胶和丁苯橡胶相比,顺丁橡胶的耐寒性、耐磨性和弹性更优异。”申松昌解释道,“丁二烯是顺丁橡胶的单体。我们这次接到的任务,就是研究、制造、生产丁二烯。长春应化所负责研究单体的聚合成胶。”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周望岳,你来说说。”时任兰州化物所二室(催化室)主任尹元根看见一言不发的研究实习员周望岳,直接“点名”。
“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丁烯氧化脱氢制丁二烯在热力学上都是有利于左移反应,而不利于右移反应的。我想反其道而行之,把反应往右移。”众人的目光聚焦到这位叫周望岳的年轻人身上。他一米七的个子,敢想敢做,是一个典型的浙江人。就在不久前,他追随爱人的脚步来到兰州化物所。
这绝对是个大胆的提议,如果走得通,这项技术将领先世界。它不同于苏联方案——用乙醇催化转化法制丁二烯,乙醇要用粮食发酵而成,在粮食供应短缺的年代该方案显得“奢侈”;也不同于美国方案——用丁烷催化脱氢法制丁二烯,该方案所需的中试设备已被西方封锁。
丁烯氧化脱氢制丁二烯能否成功,并实现顺丁橡胶的工业生产,谁的心里都没有底。听说苏联杂志上有相关报道,周望岳翻遍了图书馆的杂志,终于在上世纪50年代的杂志上找到了这篇文章,“可惜没有介绍使用什么催化剂,只说反应温度高达530摄氏度,而且反应结果不太好。我们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在装回20升小钢瓶丁烯液化气后,周望岳一头扎进了实验室。新反应问世的曙光出现了。在45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下,自制的磷-铋催化剂通过正丁烯、水、空气后,经色谱分析,获得了相当高的丁二烯收率。然而,再精进,反应结果却总是显示“不达标”。
“再来!”“再来!”周望岳并没有留时间去平复失落的心情,马上带领顺丁橡胶科研小组开始下一次实验。他的灼灼目光中仿佛升起了一团火,那是顺丁橡胶科研小组成员的希冀,也是国家的殷殷期待。
“第98次,成了!”1962年年中,新加入团队的李树本提醒大家。第一代丁烯氧化脱氢制丁二烯所用的催化剂——磷-钼-铋催化剂终于在实验室获得了成功,所有人兴奋地抱在一起。
1963年夏天,周望岳代表单位在全国第一次催化报告会上,报告了磷-钼-铋催化剂的研究进展。这是一个各国教科书上从未出现的新反应,是全世界没有先例的新工艺,与已经工业化的丁烷催化脱氢相比,其工艺简单,效果却好得多,这在会场上立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周望岳研究催化剂丁烯-丁二烯吸附机制。周望岳供图
冰火两重天
1965年8月,周望岳举着“锦州石油六厂”(以下简称锦州六厂)的牌子,在火车站口接锦州六厂一行六人。恍惚间,他在锦州六厂的队伍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高高大大、中原汉子面相,那不是他在大连工学院的同学、时任锦州六厂工程师张国栋吗?
“你来也不告诉我?晚上我请你吃兰州牛肉面。”同学见面分外亲切。
1963年,国家科委批准了“顺丁橡胶中试开发项目”,各大橡胶厂纷纷向兰州化物所抛来合作开展中试的“橄榄枝”。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研究院第一个采用固化床反应器完成了中试试验。
时任锦州六厂厂长王国斌此行是来商量能否采用另一种方式——恒温挡板流化床反应器,参与丁烯氧化脱氢制丁二烯中试合作。“多一条腿走路,自然是好事。”尹元根心想。他们马上请示中国科学院,请求批准在兰州和锦州分别开展两种反应器床型的中试。中国科学院立即复电允许合作。签完协议,王国斌当天就率队离开,周望岳、张国栋约好的兰州牛肉面也没吃上。
俩人再见面,是在当年10月的锦州。周望岳惊奇地发现,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锦州六厂丁烯氧化脱氢制丁二烯及丁二烯聚合的全部装置就已建成。“我们可是一回来,就一鼓作气搞建设。”张国栋告诉老同学。“那我们马上下车间!”周望岳也不甘落后。
11月的锦州,夜里零下27摄氏度、七级大风,雪仗风势,如一朵朵大棉花一样拍打在玻璃上。此时,已进入钼系顺丁橡胶研制放大试验的关键环节——“点火”。引丁烯、空气和水蒸气入催化床,装置开始升温运行。
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喊:“反应系统的冷水管结冰堵塞了!”
“没有办法,只能人工解冻。”张国栋边说边张罗。
周望岳等人进行了一场接力,最前面的人爬上2米高的管架,每个人小心翼翼地提着一个开水壶,浇完一壶开水,立刻撤下来进屋暖身子,再换另一个人上去。花了半天时间,水管才解冻。“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全都冻成‘冰棍’了。”周望岳打趣道。
还有一次,周望岳接到一通紧急电话,匆匆往车间赶。他一看,“不好!反应器差点变成了‘炼钢炉’”。容器通红通红的,就像张开的血盆大口,准备吞噬一切。“所有人,快跑!”他大喊。那一次意外,差一点把在场所有人都炸死。事后追查原因,是工程师监管疏忽。
冰火两重天,这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体验。

1983年,顺丁橡胶工业化生产成功后,周望岳(右)和张国栋在锦州六厂大门前合影。周望岳供图
橡胶大会战
为给下一步工业化做准备,1965年,国家科委决定开展顺丁橡胶工业化研究与开发大会战,主战场就定在锦州六厂。
次年2月,刚过完春节,中国科学院和原石油工业部、原化学工业部、原机械工业部、教育部一起组织全国34家科研机构在锦州“会师”。红旗飘扬、人头攒动的“橡胶大会战”现场,参与人员上万。
各单位的科研骨干都拿出了“看家本领”。其中,时任长春应化所四室主任欧阳均、助理研究员沈之荃负责丁二烯聚合技术和工艺,兰州化物所派周望岳负责丁烯氧化脱氢用催化剂的制备工艺和技术、反应系统的工艺和运行参数的确定等。
“全流程物料平衡测试开始!”一声令下,大家各就各位,各司其职。终于,在周望岳解决了物料“进多出少”的问题后,第三次测试获得了预期中的理想数据。会战进入设计工业生产全流程阶段,再一次明确了各部门、单位的分工。这次,长春应化所负责对镍系纯溶剂、催化剂进料工艺、连续聚合挂胶堵管等三大问题进行攻关,锦州六厂负责建设万吨级工业装置,兰州化物所继续负责催化剂性能等攻关。
1966年9月30日,锦州六厂诞生了我国第一块顺丁橡胶。在一个不到200平方米的厂房里,灯火辉煌,一块顺式聚丁二烯胶料经挤压干燥成为一个新产品。这是我国诞生的第一块合成顺丁橡胶,共50公斤。后来,它被制成一个900-20型号的汽车轮胎,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展出。

科研人员现场指导生产。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供图
决战1000小时
然而,受到政治形势影响,“橡胶大会战”于1966年5月被迫中止。回到兰州化物所,周望岳发现,顺丁橡胶科研小组解散了。他暂时无法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了。
但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顺丁橡胶。特别是当听说,1968年北京燕山石化总厂采用固定床生产顺丁橡胶,出现了“一堵、二挂、三污水”的问题——刺鼻的恶臭引来居民、公交车司机抗议,副产品挂焦严重、堵塞装置必须不断清理,污染物还需要用大量自来水稀释,最后该厂不得不宣布停产时,他更是坐不住了。
1973年下半年,周望岳恢复了课题组组长职务。“我想去锦州六厂开发第二代丁烯氧化脱氢催化剂。”渴望回到顺丁橡胶战场的他主动请缨。可当时他的妻子董坤年染上了肝炎,他不知道如何开口向她说去锦州的事。
“你去吧!这是你一直以来的科研梦想。”董坤年率先开口,全力支持丈夫。
“那你怎么办?”这是周望岳少有的“举棋不定”。
夫妻二人决定“分居两地”,董坤年带着大儿子回昆明娘家休养,周望岳带着一对7岁的龙凤胎和9名科研人员去锦州开发第二代锡系催化剂。可没过多久,紧张的科研工作让他不得不把龙凤胎送回妻子身边。
周望岳和课题组成员陈献诚、杨凤琨等经过系统的实验研究发现,第二代锡系催化剂没有更好的应用前景,他们不得不马上投入到第三代铁系尖晶石催化剂的研制中。
经过一年半的攻关,兰州化物所科研人员终于成功研制出用于流化床反应器的铁系催化剂——H-198。“198”这个数字,意味着重复实验做到第198次才取得成功。
H-198活性高、选择性高、强度高,且反应温度低,生成有害的含氧化合物和炔烃少。1981年,该催化剂经中国科学院鉴定,在国内首次成功开发了丁烯氧化脱氢用无担体铁系尖晶石催化剂,成功解决了“一堵、二挂、三污水”问题。
原化学工业部还将其写进战略决策:“根据国情,在我国利用石油气裂解分离碳四组分制取丁二烯,不会有更多增加,比较现实地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发展丁烯氧化脱氢法生产丁二烯,势在必行!”这给周望岳领衔的课题组吃了一颗“定心丸”。
相比较美国采用的固化床生产工艺,流化床的优点在于可大幅度降低有害含氧化合物的生成,这就意味着污染小很多,但它也存在催化剂强度差、易粉化等要害性问题。1000小时以上催化剂寿命实验(以下简称1000小时实验),是确定其长期反应性能的关键。
1982年2月,1000小时实验正式启动。1000小时实验必须连续进行,中途不能停车。课题组以三班倒的方式工作,谁都不能请假。第六次实验运行到700小时的时候,流化床里一向平稳的催化剂突然沸腾起来。凌晨4点,夜班人员急忙把睡在一楼的周望岳叫醒。
“不好,是连接预热器和反应器的硅橡胶管裂开了,反应气正在漏出。”周望岳顾不上想太多,马上躺在地上,挖干净硅橡胶,再换上新的硅橡胶管。这个过程远比想象中漫长,历经37个小时,他中途只喝了几口水。同事们都赞他,“真是条铁打的汉子”。
铁打的汉子炼出了“真金”,经过科研团队不懈努力,1000小时实验最终获得了成功。

锦州六厂顺丁橡胶脱氢反应装置。兰州化物所供图
举起特等奖奖杯
然而,实验室中的1000小时,与大工业中的1000小时放大实验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在失败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周望岳,遭遇到了项目中最大的“雷”。
1000小时实验成功后,兰州化物所再一次成为齐鲁石化橡胶厂、岳阳橡胶厂、燕山橡胶厂等争抢合作的“香饽饽”。周望岳、时任兰州化物所科技处副处长方展盛还是选择了“老伙伴”——锦州六厂,进行铁系第三代催化剂工业放大实验。
1982年4月,第一次开车就出现“熄火”现象,仅运转54小时就被迫停车。第二次、第三次……开车到第五次仍不成功。
“周望岳到底行不行?”下午3点,工人议论着跑光了。空荡荡的车间里只剩下周望岳和张国栋两人。
平时抛硬币猜正反面、打篮球,科研人员和工人总能玩到一块儿,可是这一次双方却各执一词。
“有可能是反应器老化造成的,我们希望检查设备。”
“也有可能是催化剂的问题,之前的检查都没问题,我们拒绝拆装。”
夜里北风呼啸,周望岳、张国栋回忆往昔,无心睡眠。
为了节省成本,他们下班后骑着自行车,“淘”遍了锦州大小工厂,从自行车铃盖、热水瓶外壳厂商手中购买薄铁皮废料,硬是将中试成本从10万元降至1万多元。
杨凤琨的儿子出生了两个月,还没有见过爸爸;陈献诚的妻子卧病在床,父亲患有严重眼疾,右眼已失明;周望岳更是连续两个春节留守锦州,对影自酌,饮尽对家人的思念……
20多年的青春倾注在顺丁橡胶上,他们已不再是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模样。
失败的消息传到兰州。时任兰州化物所副所长金振声急得当天就率队赶赴锦州六厂给科研人员打气:“实验室里有成百上千的催化实验项目,能上中试、投入工业化的实验屈指可数,这点失败算得了什么?”
张国栋对周望岳信任有加,这一次他依然选择站在科学家这边。见道理说不通,他一狠心撤换了车间主任,又重新配备了技术人员。
周望岳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一一排查。当排查到反应器时,他们发现8组内冷管中,有5组的封头掉在底板上,导致5根管子的冷水泼到催化剂上面,催化剂无法达到所需的300摄氏度,进而熄火。原因终于找到了。
1983年5月,第六次开车顺利运行到第60天、1372小时。“成功了!”泪水模糊了周望岳、张国栋的双眼。
试生产获得成功!正式生产获得成功!当年就上了万吨装置!年产量翻番,一年收益千万元!……好消息频传。
1983年12月,在丁烯氧化脱氢新催化剂(H-198)中间试验鉴定会上,鉴定委员会主任、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华郑重宣布:“H-198催化剂流化床技术在反应温度低、水比小、炔烃生成量少、无有机酸生成以及含氧化合物等方面,优于美国Petro-Tex绝热固定床技术,已跨入世界先进水平。”
截至1984年底,我国顺丁橡胶总产量达47.63万吨,总产值达22.86亿元。顺丁橡胶工业生产新技术的问世,打破了国外的封锁和垄断,是我国石油化工领域第一个完全自主完成的生产工艺。
1986年,周望岳、张国栋再次来到人民大会堂。4年前,他们在这里接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证书。
这一次颁布的是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顺丁橡胶生产新技术”项目荣获特等奖。兰州化物所和锦州六厂为并列第一完成单位,周望岳和张国栋为并列第一完成人,获奖主要单位为兰州化物所、锦州六厂、长春应化所等7家。
举起5公斤重的奖杯,周望岳、张国栋这对“顺丁橡胶兄弟”相视而笑。20年前没有吃成的兰州牛肉面,兄弟俩终于可以一起踏踏实实地吃上一顿了。

周望岳手捧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奖杯。周望岳供图

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奖杯。兰州化物所供图